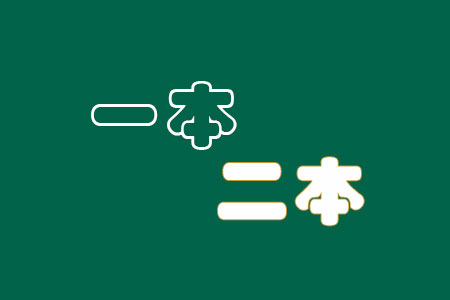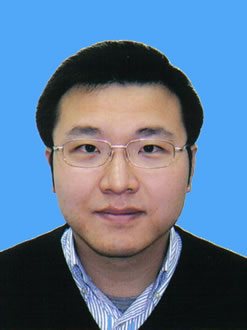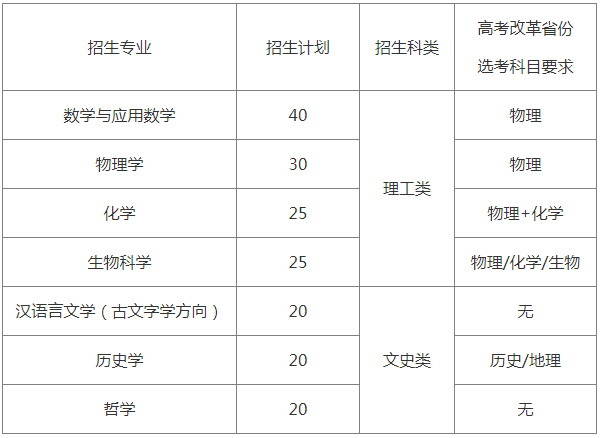《请客》
在《请客》这张照片中,杨文彬借用了《最后的晚餐》的构图。当时他的好朋友为了庆祝女友艺考成功,请全班同学吃饭,杯盘狼藉之后,所有人按照《最后的晚餐》站位摆拍了这张照片,“年长的人或许会觉得这样的模仿与结构太不庄重,以后的年轻人又或许会觉得我们的模仿很过时或很低级,但这就是我们这代人会做的事情。”杨文彬说,因此当有人问他为什么拍摄《大学社会》时,他便按照这种逻辑回答道“我就是在面对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
“头脑中唯一的想法是‘成功’,内心里仅存的感触是‘焦虑’。”美国作家亚历山德拉·罗宾斯这样概括美国“优等生们”的生活。
中国大学生的现状又是如何?鲜有人关注。
在过去两年间,中国传媒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杨文彬,成为这个群体的记录者。他拍摄他们的衣着、活动及娱乐方式,试图从中了解这个群体的内心感受。在杨文彬看来,中国的大学生是一个尴尬而不受关注的群体。
“我们一直在模仿想象中的成人社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我们也并不知道,这是对的,还是错的。”

《大学社会》
在闪光灯的曝光下,假山的轮廓、质感、层次在夜晚都展现出另一种狰狞生硬的样子,与最初设计的传统美学象征向背离。站在假山上的是学校街舞社的成员,他们穿着统一的队服上衣和展现各自特色的下装,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与个性展示的冲突,或许这也是告别十二年高负荷应试教育,忽然进入无拘无束的大学后,每个人内心发生过的猝不及防的冲击。
存在的焦虑
拍摄的缘起,是初入大学的一场校园歌手大赛颁奖。杨文彬陪朋友去参加,一个人闲逛到幕后,看到一队获奖选手正用手机自拍合影。那个场景瞬时触动了他:十几个人试图通过一个直径1毫米的自拍镜头挤进一个五寸大的手机屏幕,但每个人的衣着、表情、动作又都不一样,“是种共同的生猛气儿和迥异个性的对比”。
杨文彬突然觉得,大学正如一个舞台,所有人都渴望在这个不大的舞台上,获得与众不同的亮相。“不如记录这个舞台吧。”他想。
杨文彬最初的计划,是通过记录5个工作人员筹办晚会的过程,展现大学生活的舞台色彩。在与这5名被记录者联系的过程中,他也正经历着初上大学的困惑:“上大学到底为了什么?”在他看来,周围的同学都表现得十分自如,一副很知道“在干什么”或“要干什么”的样子。但在与被拍摄者联系的过程中,杨文彬渐渐发现,类似的困惑存在于每个人心里。
一次,他去拍摄学生会开会。一位学生干部发言说:如果不参加学生会,我这四年干什么呢?会议的后半场,杨文彬什么也没听进去,脑海中回响的都是这句话。
如今,他可以清楚地陈述出这句话背后的含义——“那是一种存在的焦虑”。存在的焦虑固然存在于人生的各个阶段,但这些初入大学的年轻人,刚刚脱离了成年人主导的学习和生活,突然开始自己掌控一切,于是本能地抓住可以抓住的一切,以便释放这种从天而降的“自由”带来的无所适从。
最常用的手段,是参加各类学生组织。
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学生会是不可回避的存在。有人以参加、竞选、留任为荣,也有人对其背后隐藏的类官场文化不屑。但从迎新、军训到全校级的歌手大赛等,大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又少不了它。
中国高校的学生会最早是纯粹的学生自治组织。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日俄为占领中国在东北发动战争,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丁开嶂在校园内成立了“抗俄铁血会”,组织抨击俄国、保卫家园的反战活动,成为学生会的雏形。
五四运动是催生学生会的关键力量。为了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与日本,北京城内各高校的学生决定组织联合行动。随着运动的推进,1919年11月,清华大学决定改选运动初期成立的清华学生代表团,以便与学界共议运动事宜。
1919年12月23日,清华全体学生聚集在饭厅,举行学生会成立大会。校方一度想以关掉电灯来迫使成立大会无法举行,但学生会依然在几支蜡烛的照耀下成立了。这届学生会成员不少后来都成为著名人物,如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
随着国家命运的变化,如今学生会定义是,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在各院校的团体会员机构。在《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中,对学生会的描述是:“学生会、研究生会是学生自己的群众组织。凡在校的中国学生,不分民族、性别、宗教信仰均可为学生会、研究生会会员。”
学生会在大学校园的角色因此也亦官亦民。但普通学生感受更多的,还是其官方色彩。杨文彬大一时经历了一次学生组织的“训新”。“训新”,意为向新生训话,通常由学生会的资深成员主持。一位学长像教导主任一样,以过来人的口吻对坐在台下的新生们说:今后一切要服从师哥师姐的命令,如果不服从,现在就请出去。
杨文彬体会到了“权力”与“禁止异议”的味道。在后来的作品中,他有意利用照片与微信群聊天的截屏表达这种感受。
比如,在一张题为《VIP》照片中,左侧是晚会礼仪小姐的合影,右边配以她们的微信工作群。晚会礼仪小姐着装统一,微信群内的头像也整齐划一。

《VIP》晚会礼仪小姐的合影
《签到》是另一张同质照片。报告厅内是统一身着白衬衫黑外套的学生会各级干部干事就坐,搭配的微信群截屏中,所有人在“签到要求”下面“队形统一”地回复:收到。

《签到》
校学生会召开的新学期第一次全会,右边的微信截图为签到通知。
什么是成功?
几乎所有人上大学的目的只有一个:成功,包括杨文彬自己。通过上大学,他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爱好,成功地脱离了家庭的掌控。
1996年出生的杨文彬高中在山东济宁的一所住宿高中就读。家人希望他学习理科,杨文彬不感兴趣,更倾向于选择文科。为鼓励他,父母花了4500元为他买了一台入门级单反。他开始疯狂地拍照,在学校附近一处公园里对着荷花池练习对焦,还接了为学校拍宣传照的“官方工作”。以拍照为由,杨文彬时常翘课,当然,拍摄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学校活动。
山东是中国的高考大省,高二正是备战高考的中场,杨文彬却享受着摄影带来的挑战与满足。化学老师因此讥讽他,“以后只够上济宁职业技术学院。”这使杨文彬开始审视自己的未来。经过审慎分析,他认定,他无法接受到一所理工科院校学习不感兴趣的课程,为继续自己的爱好,上一所文科大学“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我现在就在阳台,不让我转文科,我就从这儿跳下去。”杨文彬给父母发出了“威胁”短信。
他顺利转去了文科,并开始理直气壮地看课外书,从刘瑜、木心读到熊培云,从海子、北岛读到曼德尔施塔姆,从《动物庄园》《1984》读到《小逻辑》。他与班主任政治老师直接讨论“真理性的存在”,和语文老师通过微博聊读书,升学与兴趣突然间实现了完美结合。2014年,他以专业第一的成绩,申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名额(共有23人),进入了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
对于更多年轻人来说,成功,究竟是什么?是无法在大学校园里找到答案的。但这是一种渴望。
校园中随处可见这些渴望的影子。有早上5点就在自习室复习的考研生,有练舞到深夜的舞团,或是上课点名时几乎从不在场的学生创业者。

《开场舞团队》
更多人怀抱的是明星梦、导演梦。他们将自己表演或导演的作品发送给各高校表演系的社交媒体,以期被认可采纳;也有人先在校园内组团“出道”,从接小型商业节目开始,慢慢被经纪公司发现并签约。
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对成功的定义也在改变。杨文彬曾计划和一位同学拍摄一部关于艺考生的纪录片,但项目刚开始,那个同学的女友便来到北京,为了负担两人在北京的生活开销,这位同学接了越来越多“游戏角色设计”的商业工作,渐渐远离了他们共同的目标,纪录片也因无暇顾及而搁浅。
模仿成年人,是靠近成功的渴望的重要方式。他们扎着领带、穿着西装、夹着皮包、戴着腕表,他们按照成人社会组织活动,他们面试、开会、安排任务、选举、聚餐、举办娱乐活动……“但大家只是在模仿自己脑海中社会运行的样子。”杨文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想象身份》
在一次VIP主题晚会中,两名学生管理人员守在报告厅的门口,阻止没有门票的学生进入。杨文彬恰好在现场,从报告厅内部拍下了这两个“守门人”的神态:一个倚着门框、叉着腿,一手扶着门把手,一手刷着手机;另一位则低头玩着手机。门外,是焦急得不知如何进入的同龄人。杨文彬突然觉得,“这道门,形成了一个界限,一边是有权参与,另一边是无权介入。而大家却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
关于成功的想象,有时也会变成另一种形式。
杨文彬的一位师姐曾在学生会工作。她向杨文彬讲起,一次活动后,她站在舞台上作总结。最后无话可说时,她拿着话筒喊“学生会”,在座者齐喝:牛逼!台上诸位干部鞠一躬。再喊“宣传部”,再喝:牛逼!再鞠一躬,如此反复。
就在其中的某个瞬间,这位站在舞台中央、拿着话筒的师姐,猛然惊觉:“我不就是一个神经病嘛!”她轰走了所有人。后来,她也离开了学生会。

《学生会选举查票》
迷茫
更多人是在迷茫中度过的。
拍摄过程中,杨文彬与一些干事聊过天。干事处于学生组织最底层,通常由大一新生担任,所分配的工作多是搬桌子、买水、献花等琐事。不少人向杨文彬抱怨过,自己也搞不懂到底在做什么。
另外一批人则迷失在电子屏和虚拟社交中。大家通过移动互联网传递着图片、音乐和简短而不连贯的文字。正如美国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教授马克·鲍尔莱恩描述的那样,“从同龄人的注目中获取快感,作为生活的依靠。”
马克·鲍尔莱恩在其著作《最愚蠢的一代》中考察了千禧年后成长起来的美国年轻一代,认为相比于过去,如今的年轻人“沉浸在更加即时的现实当中”,“把朋友、工作、服装、汽车、流行音乐、情景喜剧和社交媒体之外的所有东西都拒之门外”。
在杨文彬眼中,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国内的大学生们。电子屏也成为大学生最重要的社交手段,甚至成为了存在方式,反过来,线上社交也影响着现实生活的交流和价值判断。“网络拉低了交往的难度,也降低了交往的重要性。”他所见的大学生日常往往是:聚餐前先拍照,围桌而坐的人们先在各自的朋友圈里聊天,尽兴了,才回到现实。
在倾听了不少人的烦恼与苦闷后,杨文彬突然理解了这种夹带着焦虑的忙碌:“事情好象是这样的:只要做了一些事,这一天似乎就没有白过。”但事实呢?“或许每天晚上睡觉前,体会到的只是摇摇欲坠的感觉。”
无论如何,在拍摄《大学社会》的过程中,杨文彬自己的焦虑得到了缓解,“我通过拍照去了解别人的生活,这成了我的动力。”
但他的困惑仍然无法解决:上大学到底为什么?
“大学”一词,源自拉丁语“UNIVERSITAS”,本意为“教师和学者的社区”。相比西方,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1895年,中国诞生了第一所“国批官办”大学——北洋大学堂,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收并了于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后于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冠名“国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
在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色彩纷呈,国立、私立、教会各占一峰,其间相互沟通,人员流动自如,学生可在各校间考录、转学。盛极一时的西南联合大学,便是两家国立大学与一家私立大学,在战乱期间联合以教书育人、延续文化对抗外侮的典范。
然而,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学历经几次重整、整编及院系合并,渐渐形成今日格局,其办学使命也变成为配合国家建设,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中高等教育师资。
随着就业资源紧张化,大学开始成为一个人从少年进入青年继而进入社会的资本以及必然轨道。然而,轨道既意味着方向,也意味着体制化。
上大学到底为了什么?答案从来就不唯一。
美国作家安德鲁·德尔班科在《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中总结了三点:大学学历“成为进入熟练劳工市场的最低资格证明”,对个人的经济竞争能力有所助益,长远而言,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有帮助;其次,维持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需要“明辨是非的公民”,能够区分“煽动言论和负责任的政治观点”;最后,提供一种能够阻挡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在大学里没有教条的位置,只有对事实本身的争论,教人学会享受生活,“平息欲望”。
在杨文彬看来,这三点在中国的大学都远未完成。他尤其质疑“平息欲望”的作用。他所见到的大学,“恰恰都是在培养对偶像的崇拜和对成功及金钱的渴望”。
《大学社会》发表之后,杨文彬受到了很多质疑,有人说他将微信截图与照片组合的做法是“形式大过内容”;有人质疑他抹黑学生组织;还有人认为,所拍内容都是稀松平常的校园生活,何必过度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