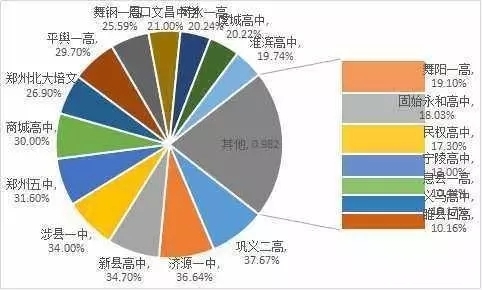胡若予
1977年的冬天,12月10日,我的老家蓬溪县城大雾弥漫,阴冷逼人。一早,我捏着两只吸满了墨水的钢笔,赶到小城边上的县教师进修学校,参加刚恢复的全国统一高考。与此同时,我的妹妹也正走进江油县的考场,异地同赴我们人生中最可珍贵的考试。
那年,我22 岁,在蓬溪一所区级中学当教师,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刚进了江油一家工厂当学徒工。我们都下乡当过知青,当时有这份工作,已然不易。12年来,在疯狂无序的时代乱象中被抛来掷去,参加高考,是想为自己做一回主。
混乱中的坚持
我和妹妹是初72届毕业的同班同学。小学毕业的1966年,文革起势,武斗完了文斗,全民疯狂,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十一二岁的少年一下子被抛到社会上,成了文化的弃儿。与“老三届”不同,我们这个年龄段,刚接受五年的小学教育,基本没有思考和辨别事物的能力,也没有清晰的理想。就我和妹妹而言,除了单纯的甚至是本能的喜欢上学读书,对于未来人生的勾画,大抵只到了读完中学上大学这一步,上大学是我们当时的唯一追求和最远的憧憬。这一下连中学都没得可上了,非常茫然,空虚。
文革来了,除了毛主席语录、诗词和著作,几乎其他所有中外书籍都被说成是毒草,被抄,被烧,被堆藏。天网恢恢,密而有漏。总有好书被热爱书籍的人藏起来,在喜欢读书的人中间秘密流传。《红楼梦》、《牛虻》、《普希金小说集》、翻得如同烂菜叶的《唐诗三百首》,都是这段时间读的。那时候借书、换书,颇像国民党政权下的地下工作者接头,会事先准备好报纸,或者红宝书空书皮,拿到书后赶紧把宝贝裹起来,或者套上红塑料书皮,溜着街边迅速回家。
终于,到1969年复课闹革命,我们上了县城关初中。开设的课程现在看来很好笑,除了语文、数学,还有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政治课。前些日子我们初中同学聚会,还忆起工基课就讲了拖拉机,大家都记得一句“拖拉机耕地,安逸得板,只要一个人,就掌握开关”。农基课呢,就学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政治课的老师好像是工宣队的,不知是啥学历,每次上课几乎就是读报。有一次讲起出身不好的人要努力改造,可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举了一个样板戏里的例子,说:“少剑波都说杨子荣是出身富农本质好嘛,是不是?”其实那句词我们人人都会唱:“他出身雇农本质好,从小在生死线上受煎熬。”对这种建立在血统论上又记忆错谬的荒唐逻辑,我们私下里偷偷传为笑谈。
语文和数学课,我们遇到了好老师。教语文的敬老师中文底子厚实,教风严谨而热忱,语文用的什么教材已经完全没有记忆,只记得敬老师在我们的作文本上划下波浪线,用一丝不苟的笔迹写下旁批和长长的总批,细心地改正字词标点错漏。我的作文时常作为范文得到评讲,我甚至从语文课上初步学习了现代汉语基本语法知识,阅读和写作自此成为终身的兴趣。而教数学的杨老师,是下放右派,北大毕业的高材生。我成人以后回想起来,意识到以他这样的学问来教初中,应是上天给予我们的恩赐,只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杨老师的数学、几何,教得真是好啊。在他的课上,脑力全开地跟着他步步求证,解题,每每兴味十足,所获得的纯智力活动的快乐至今难忘。我的妹妹同学,是我学习上最强劲的对手,每次考试,我俩成绩都相差无几且名列前茅。
1972年初中毕业,正常的话,我俩该继续上高中当同学。然而,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这看来无比正常的事,却成了空。我下乡当了知青,满心想着在农村好好表现,也许能获得推荐招工或参军的机会。至于靠推荐去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压根不敢想。两年后,妹妹高中毕业,没有工作,也没法被推荐上大学,也只好下乡当知青。她这一去,就是整三年。
我下乡后与一个五保户老婆婆同住,那年我17岁,只能算半劳力,每天挣7个工分,而10个工分才合人民币一角七分钱。我的家乡是浅丘地区,资源贫瘠,人多地少,所有能种上粮食的土地全被开出来利用,粮食还是根本不够吃。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麦收时节,各自搭帮割麦子,按所割面积算工分。我力气小,没人愿意带我,平地上大而整的麦地好收割,轮不上我,自己一个人转着坡去收割小块零星的地,大的约有两间屋大,小块的也就有如簸箕。吭哧吭哧割了几天,记分员来算面积,一共36块地,总共只有一亩。
年终分配,按所挣工分折算,我的全年口粮160斤稻子,800斤红薯(吃一半烂一半),50斤玉米。粮食不够吃,我和婆婆经常每天只吃早稀午干两顿饭,晚上就忍着。十七八岁的女孩,饥饿的感觉很不好过,有时白天干了劳动强度太大的活,比如挖板田、担砖泥等等,晚上我看书时,婆婆便抓一把豆子炒了给我加餐,而没牙的她一颗也不沾。婆婆自己有一只眼睛完全没有视力,我没去之前,天一黑她就上床睡觉了。我去以后,晚上若看书写字,她从不吝惜灯油。就这样,晚上除了有时去夜校给青年们读报教唱歌,其余时间都被我用在了读书上。每过一段时间,去县里借回来几本书,断简残篇的《古文观止》、零星的中华活页文选,还有手抄的外国诗歌,读到那些优美的诗文,会高兴得如同吃了回锅肉,反复咀嚼。经常也非常投入地写点文字,新诗或古体诗,写小散文,编三句半等等,多是战天斗地,豪迈空洞的应时应势之作,也有的时候咏景抒情,抒写内心不敢示人的真实情怀。这些没有目的不成系统的读书和写作,使那些浑噩贫瘠的日子变得不那么苦闷和无聊,也使自己保持了可怜的一点智力活动而不至于变得愚蠢可憎。
两次考试
那天,我走进高考考场的时候,浓雾还没散,即使教室窗户大开,光线还是很暗。北风夹着雾水刮进来,屋里没有生火,又湿又冷。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把钢笔放在桌上,两手指尖相对轻轻敲击,来使手暖和一点。两只手都长着冻疮,红肿之处,艳若桃李,也不敢太使劲。语文,数学,政治,史地。试卷发下来时,心一下子沉静下来,那种熟悉、笃定的感觉,好像盲眼流浪儿摸回了家门。终于,不用比背景,不用担心成份,不用仅凭组织推荐,就凭自己的知识才学,有机会为自己圆梦。盼这个公平竞争的考试,盼了多年了。
现在提起恢复高考,都知道发生在1977年。其实,更早一些,1973年的中国,已经有过一次中途夭折的用知识考查选拔人才的尝试。那一次,我也是亲历者。
那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当时采取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大中专招生除需经过评议推荐及审查、复查外,还要进行书面文化考查。我所在的生产大队就我一个下乡知青,和几个回乡知青一起被推荐参加中专考试。我的机会来了!记得当年县里的招生学校中,公认最好的是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和内江铁路学校,各有5个名额。心气颇高的我就报名这两个学校。考试的时候,语文和数学我都做得很顺利,埋头刷刷刷只管写,有两个老师进考场来,总在我身边转来转去地看我答题。不到收卷时间,我答题完毕也检查过了,自信没问题就交了卷。后来听监考老师说,我考得非常好,那两个看我答题的其实就是招生学校的人,“他们当时就看了你的试卷,很满意。你肯定没问题!”监考老师说。
高兴得太早了。在那个没有理性的荒诞年代,随时都能有反常识却能成事的人物出现。这次出来的是“白卷英雄”张铁生,生生把进行了一半的招生全盘推翻,考过的成绩没用了,重新回到老一套:推荐选拔。我们大队就推荐一个。别人告诉我,大队长和大队书记都有亲戚的孩子要上学,考试的时候没敢去,只有靠推荐,你这次就别想了。我的心凉透了。可没想到最后却意外地被推荐上去:大队长和书记各自想推荐自己家族的孩子,互不相让,让我上反倒成了他们不让对方受益而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但是我也没能进入自己心仪的学校。县革委会的头儿说,大城市的好学校让贫下中农的孩子上吧,这个知青,留在县里当教师嘛。于是,把我招到了当年刚复办的县师范学校。这种说不出来的不公,我哪里有交涉的余地?师校连校舍都没有,找了个破败的寺庙,一边建校舍一边开课教学,喝水吃粮都自己挑运,吃菜自己垦土种植。关键是没有教材,老师们虽大都尽力,也很难开展有系统的教学。尽管如此,能够在学校学习,也算万幸。我很努力,毕业时,本应去教小学的我,和另几位同学被“拔”去做了中学教师。
1977年的高考,与进考场做题相比,前面的复习简直就是拼命。
10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新闻,我一分钟没有犹豫,决定报名。这时,距考试时间只有一个多月,我一边工作一边复习——不是复习是学习,我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堪:数学刚刚有初中程度,地理、历史一片空白。我分析了自己的情况,把百分之八十的时间用在了数学上,硬是把高中数学课本全部自学了一遍,不懂就去向县中老师请教,做了1—5册全部习题(第六册太难了,也没有时间了),目标是尽量能多拿点分,不拖总分的后腿。历史、地理和政治,没条件系统学习了,县教师进修校的老师掏光家底,遍寻资源,编写了好多题,无偿提供给当年的考生,记得密密麻麻好几十页,我是用了足足三天的时间来背了个大概。而语文,则只好凭底子硬考。我的妹妹,刚费尽周折进了江油一家工厂当学徒,也在每天下工后挑灯夜战。在我的身边,还有几个一同报考的知青好友,我们抱团复习,相互打气,天天熬到凌晨两三点钟也不觉得累。后半夜回家去睡觉,走在小城黑黢黢的巷子里,冰凉透骨的冷风从身体穿过,也不觉得冷。那个时候,真的是飞蛾扑火一般,只管向着那团光明扑过去。
那场高考,考场上监考非常严格,考生也十分自觉。我所在的考场没有听说过作弊的。但考生状态大不相同。考语文时考生基本上都能一坐到底,政治和史地综合考试时就有提前退场的了,而数学考试,干脆有人就整场弃考。我的考试很正常,很顺利。
可怕的家庭出身
自己能做的事做完了。然后,是焦灼的等待。比起考试成绩,更让我寝食难安的,是政审。
那时候,人在社会生活中赖以立足和发展的硬标准是家庭出身。不同出身的人被分为三六九等,出身工人或贫下中农家庭,天然自带光环,在审查表上一填,招工上学当兵一路优先。如果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庭,就如同被黥面的罪人,低人一等,步步艰难。我的父母都是新中国初期参加工作的普通干部,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我和妹妹随母亲生活。母亲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尽管她同那个时代其他同样出身的人一样,声明与家庭划清界限,但这个包袱还是成为她大半辈子的阴影。我们虽然连外公长啥样都从没见过,在填表的时候“家庭出身”一栏也必须填写地主。而父亲家,是下中农。
初中时,我是学生干部。学校要发展第一批共青团员时,我很积极地报了名。当时学校仅有的几个团员老师组成支部,开发展大会,递交了申请的学生悉数在场,一一当面宣读自己的申请书,团支委表决通过与否,气氛相当庄严。前面的同学都获得了通过。轮到我了,响亮地念完申请书后,略为紧张地期待着接下来的表决。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支委中的一个老师站了起来,阴沉的脸上布满寒霜,眼睛像钉子一样扎过来,盯着我开口了:“对这个同学不忙表决,我要问她一个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我有点懵,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你的家庭成分是什么?”“地主。”我心里什么东西在崩塌。“为什么是地主?”“因为我父母离婚了,我跟妈妈,妈妈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我努力回答。“那你父亲的家庭成分是什么?”“下中农。”我觉得自己没有力气了。
支委老师突然提高了分贝:“问题来了。你为什么放着下中农出身的父亲不跟,而偏偏要跟地主家庭出身的母亲?说呀。这是什么阶级立场!”五雷轰顶。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能回答!那不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能够回答的问题。也不是她应该回答的问题。我终究没能入得了团。
多年以后,我知道了那位老师自己的出身也很不好。那么,他那样做许是为了自保。我不怨他。但是这个出身问题,却一直纠缠着我。每每需要填表,政审,都饱受煎熬。这一次,政审会是挡住我去路的巨石,还是被新的洪流冲击到一边的稻草?高考,是真的唯才是举,还是再一次叶公好龙?
等待。度日如年。
录取了,又差点放弃
转过年来的春节期间,我们在成都的亲戚家过年。一天在表舅家正吃团圆饭,邮递员送来挂号信,是吉林大学招生办公室寄来的。在座的十几个人都屏住呼吸,眼睛齐刷刷落在表弟手中快速展开的信纸上。“我被吉大录取了!英语系,我被录取了!”表弟一喊,在座的十几个人欣喜若狂,好几个人霎时泪盈眼眶。我和妹妹互看一眼,马上夺门而出——买车票,立即回去等通知。
从成都到家乡,要坐11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我早已不记得是怎样挨过这11个小时的,只记得一路上滴水未进,头脑里却像有一团火球在滚来滚去,灼得全身发烫。回到县里,通知未到,一夜无眠,辗转到天明。
第二天,通知来了——四川大学中文系,第一志愿!我攥住录取通知书,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把命运攥在了自己的手里。我奔到邮局,按事先约定给在江油的母亲和妹妹发去电报,等我从邮局出来,消息已传遍县城,人人都向我祝贺,到处都是热情的笑脸。下午,妹妹的电报到了:“祝贺姐姐,我也被重庆大学机械系录取。”喜悦和兴奋达到了顶点。
我、妹妹、表弟如愿以偿进了大学。我的同学中有老知青、农民、工人、教师、军人、在校学生……每个人都与我一样有一部伴随国家命运起落沉浮的奋斗史。这就是发生在1977年冬天的事。有这么一批最小十五六岁最大三十出头的青年接受了历史的挑选,通过公平的考试走进了大学的校门,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逆转。他们叫七七级。
七七级,包括其后的七八级七九级,到今天已成了一个专用名词。对于社会,她标志着荒谬的反智价值观被清算,标志着公平公正尊重知识的人才选拔机制的恢复重建,科学、理性的教育观和教育制度自此复苏。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则意味着从公正的选拔机制中获得了可把握的实现理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途径。那个辉煌的时期,人性的唤醒与回归,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念的启蒙与求索,对我而言,宛若新生。从那以后,我追求着光明的生活和人生价值,活得勤勤恳恳,堂堂正正。
当年的我们从长达十几年的公然反智时代踉踉跄跄走过来,知识背景残缺断裂,在长达一生的时间内都在持续弥补,思考能力在痛苦的审视、反思和否定中一点点获得,回归常识的价值体系在开放和保守的混乱冲突中缓慢建立。我们的同学中,有数位博士生导师,有成功的企业总裁,有各级岗位的领导人物,有坚守文学的作家,更有许多像我一样在教育、新闻出版、文化事业、国家机关工作的普通工作者。个人的发展际遇不尽相同,欢欣和烦恼也往往如影随形,但是,前行的指向却殊途同归,那就是尊重和高张民主与科学,宏扬人性与理性,终身不断地学习进取,让自身与社会同时发展得日益正常、健康、和谐、美丽。
一次高考消除不了历史的沉疴,但是会留下印记。40年过去,被1977年那场举国瞩目的考试聚拢的高光渐渐隐去,理想的色彩屡经消磨,早已融入当今社会的斑斓异象之中。也许,作为当代史研究的一个方面样本,1977年高考群体会不断被提及,被关注。我们这些当年考生的个人命运实现了突破,但社会变革的成功却并非像我们毕业时以为的那样指日可待。七七级的主体是“老三届”,出生于革命后的,重生于改革开放的大转折,被天然涂染上我们国家每个历史阶段的色彩:亮色,暗色,杂色,丰富而含混。我想,七七级也许是过渡的一代。关山隐隐,江流回环,无论社会发展如何曲折,即使在这一代手中没能涂抹成理想的新画,七七级也会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底色存在,厚重又明亮,历久而不衰。
(作者系1982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曾任中国农业出版社编辑,国家开放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