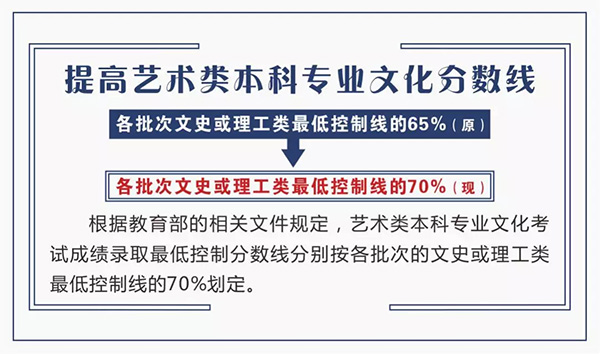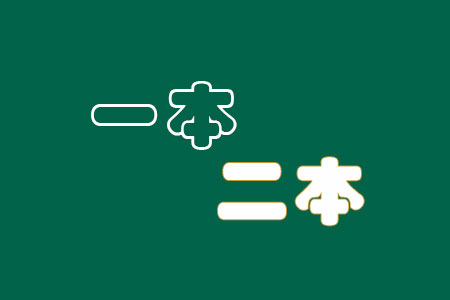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亲眼见证国家由弱变强感到幸运
更新: 2019-10-09 19:12:35 | 人民网
在刚过去的那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我有幸作为嘉宾见证并参与了庆祝新中国70华诞的盛典。在天安门广场北侧的观礼台上,一种想和人分享的冲动油然而生。 1992年10月,我作为政府公派学生到日本京都留学。我所住的左京区元田中町,据说就是曾为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当年在日本研究甲骨文时生活过的地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时尚属热血青年的我感慨万端,如鲠在喉,便给在国内的恩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多年之后,我们还是摆脱不了到人家的国度留学的命运,什么时候,我们能让人家来咱们中国留学呢?后来恩师把这封信拿到学校的报纸上刊发了。 1999年7月底,我学成归国。夜晚,轮船行经濑户内海,朦胧中看见巍然屹立的濑户大桥。它连接本州和四国,横跨在头顶的星空下,是日本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不无羡慕地对我爱人说,我们国家不知什么时候能够造出这样气派的大桥?回来之后,2001年我去香港出公差,学生开车带我参观,其中之一就是香港新地标——青马大桥。这座桥和日本濑户大桥外形相似,也是钢索吊桥结构,气势恢宏,且在1997年就落成了。我顿觉两年前经过濑户内海时的感慨,纯属孤陋寡闻。之后,我在大桥桥端的碑石上,看到设计者和建造者均为外国公司,心中还是隐隐失落。 让人欣慰的是,最近20年来,在中国,那种用粗壮钢索悬吊起来的大桥早已不稀罕。据当年一起负笈东瀛专攻建桥的同学讲,杭州湾大桥、青岛胶州湾大桥在长度上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不久前建成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则是世界第一,明年即将通车的平潭公铁两用跨海大桥也即将超越濑户大桥了。甚至连高速列车这种当时在日本乘坐一次就足以对人炫耀许久的“神器”,在当今中国的大地上也已是四通八达,甚至比日本的里程还长、速度更快,更便捷。 这些年来,我常因学术交流到日本去,也会生发出一些感慨。尽管日本的天空还是一如既往地空澈澄碧,地面一如既往地不着纤尘,日本人的脸上还是那种波澜不惊的微笑,但这些已远不及20多年前我初到日本时那般震撼人心了。 1992年10月2日,抵达日本的第二天,我们一行8人乘坐一辆面包车在倾盆大雨中从大阪的伊丹空港驶向京都。在京阪高速公路上,或许是因为初来乍到一个让父辈铭心刻骨而我等却充满憧憬的国度,大家还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所笼罩,一路沉默不语,直到湿漉漉的车窗外一辆出租车一闪而过,有人发出连出租车都是丰田皇冠的惊叹时,气氛才稍微活跃起来。想象和现实完全一致,我们真的已经到达此行的目的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要知道,拥有一辆丰田车,恐怕是当时国内一般百姓一辈子的奢望——我大学毕业时得到的一个祝愿礼物,就是一辆丰田车模。这个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多年以后漫步日本街头,我还会想起那满街都是丰田车的视觉效果。回忆归回忆,如今我却觉得这些车有些瘦小、单薄了。 每次回京都时,我都会到当年住过的地方看看。那幢建于上世纪50年代、伫立在鸭川河边、据说住过驻日美军的两层木结构房屋现在还在。镂空的木条镶嵌着的毛玻璃门里,挂着亚麻色的门帘,一副京都民居特有的悠然宁静之美。只是木质的门柱更加灰暗,裂纹更深更长了,门口悬挂的户主铭牌上已经换作了本国人。这是一个位于日本重要文化遗址下鸭神社附近的社区,有公务员宿舍、小学、高档餐厅,还有深墙大院的私宅。和日本这个国家近年来的整体经济状况一样,我当年住处的周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时光在这里几乎有一种不流淌的感觉。 虽然人们常说,日本直到现在仍在泡沫经济瓦解之后的泥沼里挣扎,尚未脱身,但从其科研和教育来看,情况似乎没有那么糟糕,甚至完全相反。距离我原来住所步行约30分钟、与日本的旧皇宫京都御苑仅一路之隔的地方就是我当年就读的大学。那是一所创办于1873年、奉行良心教育的教会大学,其创始人新岛襄被誉为“日本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他16岁时偷偷跑到美国阿默斯特学院留学,毕业回国立志创办一所培养“一国之良心”的学校。经过几代人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所学校现已成为载入日本中学历史教材的私立名校。 在日本传统宗教神道教中心京都旧皇宫的北侧、宋时从中国开封归来的留学僧创建的佛教圣地相国寺的南边,高耸的尖顶钟楼之下,绿树成荫,一幢幢洋溢着浓郁英格兰风情的红砖建筑掩映其中,错落有致。在这块三教鼎立、交相辉映的风水宝地,西装革履、不拘言笑的教授和衣着时尚、青春洋溢的青年,在和煦的阳光下,三五成群,或行或席地而坐,其乐融融。这是我对这所之后生活了7年的学校的最初印象。来日之前,我还为分派到一个并非自己所愿的私立学校而有些沮丧,但置身其中之后,时间越长,就越为自己感到庆幸,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将东西方结合的理想环境。一定要说有什么不满,那就是校园太小。 “从没见过这么袖珍的大学——也就我小学时的校园那么大吧。”我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但只要想想便理解,毕竟,这是一个国土狭小的地方,又是在京都御苑相邻的寸土寸金之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毕业之后,校园面貌已经大为改观、今非昔比了。原来盘踞校园中心的附属中学被另迁他处,取而代之的是若干栋与周边环境浑然一体的红色西洋风格的建筑。据说为了和校园整体风格神似,盖房子所用的红砖还是专门从英国定制的。更叫人称奇的是,京都最为繁忙的地铁乌丸线为大学专设一站,车站就在大学校园的地底下,乘客下车之后乘坐升降电梯可以直接抵达大学的食堂、书店和超市。这样,来自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游完京都的旧皇宫、相国寺之后,到大学的食堂里吃饭、喝咖啡,稍事休息之后,就在满眼西洋风情的大学校园里徜徉了。这是何等惬意的事情! 这几年,我每次回学校,都要回母校走一走,在为变化感到惊喜的同时,也在疑惑这背后的经费来自何处。要知道,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裂之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很多高校特别是私立大学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终于有机会,我向曾担任学校法人总长16年之久的导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开玩笑说:“你终于发现,我们这所大学是个不错的大学了吧!越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气越旺,这是最好的口碑。”留校做教授的日本同学告诉我:“和中国的家长一样,日本家长也认为,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经济越不景气,越要在教育上下功夫。因此,这些年来私立名校行情看涨。”原来如此! 由此我不禁想起另一件旧闻。2001年,日本政府宣布,计划到2050年收获30个诺贝尔奖。当时,包括我国媒体在内,许多媒体看笑话,说日本政府又在口出狂言。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到去年为止的18年间,已经有18位日本人将诺奖奖牌收入囊中。看来,表象之外,在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教育和科研方面,日本丝毫看不出不景气的迹象。 不久前,我参与接待了一个日本访问团。晚宴时,我恰好和一位经营过企业、转行到大学任教的日本学者坐在一起,聊起中国最近的变化。他说,从上海过来,乘坐京沪高铁,感觉好极了。他还说,在日本,铁路经过之处,由于土地私有制,征地非常困难,导致日本新干线线路弯弯曲曲的地方很多,速度上不去。他补充说,日本东北地震之后,6年过去了,还有很多灾民住在简易救灾房。这不是因为日本政府没钱,还是因为体制。因为要让灾民从海拔低的地方搬到高处,涉及征地、通电、通水、修路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预算。而做预算在日本要经过很复杂的程序。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正值我留学回国服务20周年。常有人问我,如果当年没有回来,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我私下也不止一次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在日本某个私立大学谋个职位,向日本学生教授一下中国法的基础知识。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上课时可能也会时常调侃下自己的国家,以迎合课堂上的学生和周围的同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而我现在,在自己国家一流的高校里,和优秀的同行共事,和优秀的青年人教学相长。这不正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最高化境吗?难怪我的日本导师和同学都说我当时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我不是一个有很高觉悟的人,也不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我的存在对于这个国家来讲或许微不足道,即便如此,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还是情不自禁,为生在能亲眼见证国家由弱变强的时代感到幸运,也为自己能够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为国家尽微薄之力而感到自豪。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大学排名 985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