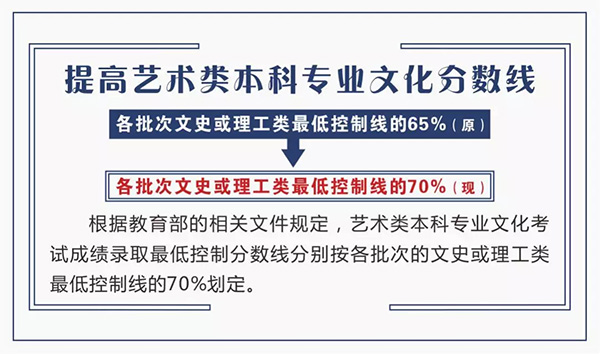2017年11月15日,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就一起涉嫌盗窃罪案开庭审理。当天的庭审实现了检察官指控、当事人出庭、法官审理等庭审三方的异地实时高清视听音频连接。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罗聪冉
8兄妹分家析产,当事人5个在宁波、2个在杭州、1个在广西,且8人均已年迈,最小的妹妹都已有60多岁,有的还卧病在床——对于这起案件,召集他们在一起调解,其中的艰难不言而喻。
如今,借助互联网技术,动动手指就可以搞定——在法官的指导和亲属的帮助下,8兄妹进入“移动微法院”平台,经多次调解,最终8位老人在线签订了调解协议并签收调解书。
这样的审案在宁波人民法院早已不是新鲜事。
这只是近年来智慧法院司法便民的一个缩影。在时下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司法改革中,人工智能将如何服务法院审判?又会给司法改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从“让当事人跑”向“让数据跑”转变
整个法庭上只有法官和书记员,原告、被告及其代理人都没到庭,但诉讼程序依然顺利开展——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去年9月打造的互联网法庭,通过远程庭审系统实现法官与当事人“隔空对话”已不稀奇。
西城法院信息技术办公室工作人员马兰介绍,庭审前当事人只需要提前准备好接入设备,在收到庭审提示短信后,按照提示短信中提供的下载地址,在设备上下载并安装庭审应用,确保网络状态良好,即可参与庭审。
当事人登录时,系统会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将远程当事人的人脸画面与公安部人脸图像数据库进行分析比对,在庭审前对当事人进行身份确认;庭审过程中,支持各方参与人当庭上传证据材料,以共享桌面的方式实现在线举证质证;通过内嵌的语音识别技术自动生成笔录,庭审结束后由书记员展示给案件参与人,各方参与人核对无误后,可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进行签字确认,由法官当庭宣判。
“互联网开庭适用于跨区域类案件、小额速裁或责任清晰的案件、当事人不便到庭的案件。采用网络方式解决纠纷,成本低、效率高,做到了‘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马兰提到,目前,西城法院正在探索开发免下载的微信插件,替代现有的应用程序。
今年年初,小程序“宁波移动微法院”在宁波两级法院全面推开;随后,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宁波两级法院为“移动电子诉讼试点”。目前,“移动微法院”全国版已经在浙江三级法院全面使用,并将逐步在全国落地。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沈路峰介绍,在“移动微法院”主页上有“我要立案”“我的案件”等选项。线上立案后,系统生成一个专属办案空间,法官、原被告、代理人等都在一起。所有的举证、质证都可以实时递交,法官、诉讼当事人、代理律师等相关人员可以同时看到,还可以当即进行质证。而且,因为增加了原被告的沟通机会,调解成功率也提高了。
“以前是当事人围着法庭转,打官司奔波劳累周期长。现在,从立案到结案,老百姓只需轻动指尖,甚至无需下载,足不出户就可以在手机端实现移动的全流程诉讼。”沈路峰认为,“移动微法院”在便利当事人的同时,也给法官带来了诸多便利,程序性、事务性工作用时得到压缩,使法官能够从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处理司法核心业务。
今年上半年,宁波两级法院法官人均结案数同比增加21.85件,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下降11%。
目前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除了以上两种形式之外,记者注意到,北京、上海、河北等均推出了名称不同的人工智能法律工具。如北京法院的“睿法官”智能研判系统、上海法院的“206”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河北法院的“智慧审判支持”系统等。
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左卫民总结,纵观当前实践,法院系统在智慧法院建设中所使用的人工智能主要有以下形式:一类是信息的电子化、数据化。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上海高院、广州中院等超过100家法院就应用了科大讯飞公司所研发的智慧法院庭审系统。根据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介绍,智能语音庭审系统的语音录入转化文字速度可达150 - 300字/分钟,应用后法庭审理时间平均缩短30%至40%,庭审效率明显提高。
一类则是办案辅助系统的智能化。例如,河北高院研发的“智慧审判支持”系统,帮助法官对电子卷宗进行文档化编辑,辅助法官完成文书的撰写。还有一类是对实体裁判的预测与监督。例如,北京法院的“睿法官”系统便是依托北京三级法院统一的审判信息资源库,运用大数据与云计算充分挖掘分析数据资源,并依托法律规则库和语义分析模型,在法官办案过程中自动推送案情分析、法律条款、相似案例、判决参考等信息,为法官判案提供统一、全面的审理规范和办案指引。
不过,记者注意到,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现实呈现出喜忧参半的局面。
例如,对于智能语音庭审系统,有书记员坦言,在整理庭审记录时,智能语音庭审系统因错误率较高,很多时候都是帮了“倒忙”,“这样的识别结果,如果同步改完全来不及;而事后改,如果不重新听录音,都不知道怎么改,反而增加了工作量”。
在左卫民看来,法律人工智能在中国未来可期的中短期内只可能是一种有限的辅助办案手段,难以应用于核心的司法工作——裁判。因为法律领域中的人工智能无论基于何种算法,其基础都是有大量数据尤其是大量优质数据。
左卫民指出,人工智能开发基础的法律数据基本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裁判文书,但上网的裁判文书数量可能只有审结案件的50%,另外,裁判文书事实上只记载了裁判结论,而反映裁判过程的决策信息并未体现在裁判文书中。这意味着基于裁判文书的人工智能获取的信息其实较为有限,而依赖这些有限的信息提炼普遍的裁判模式,是相当危险的。
从事司法大数据研究的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禄生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谈道,目前,司法人工智能通过模型训练形成的算法,是建立在对海量文书学习、训练的基础上,但是,研发人员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保证训练的样本文书都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文书本身就是错误或者存在瑕疵,基于这些文书训练产生的模型与算法就可能遭遇精确性困境。
王禄生补充,事实上,一线法官因为不知道算法是什么,不清楚这种量刑预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对这种量刑预测的系统似乎有些忧虑,“这其实也是人工智能的悖论导致的,即人工智能算法的隐蔽性和案件裁判过程透明性间的冲突”。
事实上,国家层面也注意到了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的双重性。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在鼓励发展人工智能的同时,也明确提出“制定人工智能产品研发设计人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守则,加强对人工智能潜在危害与收益的评估”“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实行设计问责和应用监督并重的双层监管结构,实现对人工智能算法设计、产品开发和成果应用等的全流程监管”。
沈路峰也认为,现阶段,人工智能在事实认定方面能力较弱,很难实现由“证据性事实”向“推断性事实”的推论,再实现由“推断性事实”到“要素性事实”的推论转化。目前,法律人工智能的定位是做辅助法律人决策的助手与“参谋”角色。
他建议,今后在持续推进司法数据资源开发应用的同时,应全面确立数据标准,持续提升数据质量;打通人民法院司法数据和业务应用的外部协作、诉讼服务等应用的对接,打破法律职业间的壁垒和法律数据的封闭性;全面提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提升信息公开质量,形成司法公开的常态化和司法服务的便捷化。